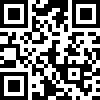《西洋镜:5-14世纪中国雕塑》 [瑞典]喜仁龙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《西洋镜:5-14世纪中国雕塑》
[瑞典]喜仁龙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唐山
“相比于西方国家的雕塑艺术,中国雕塑几乎可以说是反对人格化的。在这种艺术中,找不到那些在欲望驱使下行动的、富于个性的人。早期,描述性或说明性的浮雕非常罕见,即使在这些浮雕中,人物特征也是抽象多于写实。艺术家的才能主要体现在装饰的布局上,在大多数早期的浮雕中,装饰布局类似于绘画的构图而非雕塑的布局。”在《西洋镜:5-14世纪中国雕塑》中,瑞典著名的东方学者喜龙仁这样写道。
OsvaldSirén,喜龙仁,一位痴爱中国的瑞典人,被称为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。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,他是一座里程碑。著名学者高居翰称其为“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”,是最早“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”。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,即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,有很多汉译本。喜龙仁的名字似乎特别有“喜感”,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称他是“西冷”(一种牛排),胡适称他是“西伦”,还有学者称他是“喜龙士”……他的名字却常被写错——国内常误作喜仁龙,《西洋镜:5-14世纪中国雕塑》沿用了一直以来的误译,本文则采用喜龙仁的译法。
喜龙仁的这段话颇见功力:首先,他意识到中国古代雕塑更重程式化;其次,这种程式化与中国画息息相关。
不过,其中也充满误会:程式化不等于反人格化,喜龙仁不免以己度人。
喜龙仁显然不明白,中国古代艺术并不强调写实,而是更重视对内在的生命、心理、气质、性格等的把握,即“传神”“气韵生动”。
“传神”“气韵生动”离不开写实,但常有夸张。比如塑天王像,为彰显其威武,常取怒目式,眼珠凸起,超出正常生理限度,而胸部和四肢的肌肉又过度发达,很难让观者产生真实感。但这种塑法已成定式,不如此,则无人能识。这种塑者与观者的共识,即为程式。
中国古代雕塑重视程式,或与二者相关:
首先,古人制器,主旨在“铸鼎象物”,即“使民知神奸”与“用能协上下,以承天休”。制器必须承载教化功能,只有包含普遍道理,才算挣脱了“嬉”的层面,才有永远存留的价值。因此,创作的评判尺度就在于能否继承旧程式、探索新程式。
其次,中国画也高度重视程式,也以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为旨归。宗白华先生说:“晋、唐以来塑像反受画境影响,具有画风。杨惠之的雕塑是和吴道子的绘画相通。”
杨惠之是唐开元时期著名的雕塑家,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(著名书法家)的笔法,因吴道子的画名更盛,杨转攻雕塑。传说黄巢起兵时,尽毁长安、洛阳寺院,唯留杨惠之的塑像,以其太逼真,不忍下手。
中国历史上少有雕塑家,因从艺者劳于筋骨,士大夫鄙之,史官亦不载。杨惠之被后人尊为“塑圣”,却无作品存世(传说江苏甪直镇保圣寺罗汉群像出自杨惠之,但事实上,它们是宋代作品),他曾著《塑诀》一书,亦亡佚。
我们因拥有杨惠之而自豪,却又因看不到他的创作而深感遗憾。这遗憾源于,在中国古代,书法才是艺术正脉,雕塑属匠作之事,只在5-14世纪惊鸿一瞥,进入高峰期,此后又迅速衰落。
至于5-14世纪的高峰期,也是受佛教传入影响,统治阶级在雕塑佛像上投入甚多,刺激了匠人们的创造精神。而传入中土的佛教实出自犍陀罗,亚历山大曾征服这里,古希腊贵族在此执政两百年以上。一方面,他们将古希腊哲学的普遍主义与早期佛教相结合,极大提高了后者的世界性;另一方面,他们带来了古希腊艺术。
犍陀罗雕塑作为古希腊雕塑余脉,传入中原后,推动了中国雕塑的发展。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上,可见犍陀罗雕塑的标准特征。
遗憾的是,古代雕塑的高峰期匆匆而过,很少被国人关注,倒是引起喜龙仁的激赏。作为西方人,他无法理解中国书法,对中国画也只懂皮毛,好在雕塑、建筑与家具更直观,它们在西方被列入艺术院校的专业课中。喜龙仁从偶遇中国罗汉画(中国宋代的一个画种,已失传,作品多为日本寺院收藏,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亦有收藏,不知为什么,喜龙仁从这些画中感受到“精神力量”)开始,走上了痴迷中国艺术之路。
虽然喜龙仁对中国古代雕塑存有误会,但他用相机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影像资料,这些雕塑都是5-14世纪高峰期的代表作,如今很多已遭毁坏。作为后人,我们只能从老照片中去想象曾经。
《西洋镜:5-14世纪中国雕塑》是一座精神的纪念碑,是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致敬。翻阅本书可知:在跨文化交流中,误解、偏差、盲目在所难免,关键在于能否像喜龙仁那样,秉持一颗仰望永恒、从人类整体看问题之心,苟能如此,就注定会写出一本不朽之作,就像本书这样。